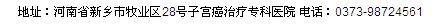先天性心脏病女孩下徐苗苗
(六)
火车本应该3月13日下午3点多到站,却晚点两个小时,直到下午5点左右,那列火车才怒吼着驶入北京西站。
我在心里暗暗祈祷,“这可能是好事多磨吧,吉兆。”
杨武成和我接到了这对患难父女,经过简短的询问,按照事先安排,医院。
医院主治医生范祥明,医院等候着我们,他是江苏苏州人,长期以来与春苗基金会有公益救助合作。
范医生有着典型的苏南人性情,温和而又细腻。
接下来的几天,医院对徐苗苗做了全方位检查,期间,医院床位紧张,直到3月15日才住下院。
3月16日是值得记住的日子,确定这天做手术!
当天下午3点,医生找徐方才谈话,将手术中可能会发生的一切风险进行告知。对于医生来说,这是例行公事,但对于病人家属来说,这是迎面高速飞来的巨石,如果接不住,就可能退缩,即使接得住,也会承担着史无前例的重压。在手术同意书上签字的那一刻,那张纸似乎就是那道分界线,将阴阳相隔。这需要很大勇气。
徐方才签了字,艰难的!
手术室门口,徐苗苗被推着往里走,就在即将进门的那一瞬间,徐苗苗哭了,她藏在内心深处的脆弱、对这道门里面的恐怖、对生活和爸妈的热爱,一时间从心底上涌,将眼睛化作出口,以泪水的方式将这一切告知所有的人。
门口的人都为之动容,徐方才应该是最难受的人,这个无助的山里人极力控制着自己,岁月和岁月路上的坑坑洼洼赋予了他自己的处事法则,他压抑着自己内心的表达,站在孩子身边,给予孩子巨大的安慰。
徐苗苗下意识抓住了我的手,不肯放开,眼泪在往外流。这丝毫没有驱赶掉她的坚强,因为,即使小手发抖,也没有发出猛烈的哭声。试想一下,一个孩子清楚的意识到,自己要去参加一场战争,很可能再也无法回来,如果不是异常的勇敢,她的表现会怎么样呢?所以说,苦难让人心智坚强,不分年龄。
她的小手冰凉,有点刺骨。
范医生体现出了一名医务人员的经验和爱心,他对徐苗苗说,“不要怕,我让你丽阿姨进来陪你!”
他向我使了个眼色,我和医生一起推着手术床进去了。
麻醉医生也非常专业,他一边做着准备,一边和徐苗苗聊天,问她“喜欢爸爸还是妈妈?”“学习成绩怎么样啊?”“以后想做什么工作啊?”等等。极度紧张的空气被驱赶一空,徐苗苗也放松下来,借此时机,医生给她注射了麻醉。
没过多时,她体内的麻药奏效了。我离开了手术室,和他的父亲在外面等着。
出来的时候,麻醉师告诉我们,去等候区找个地方坐下,没有意外的话,手术预计需要四、五个小时。
(七)
楼下等候区里有不少人,都是其他病人的家属,每个人脸上贴着一张严肃的皮。有几个坐在椅子上,弓着背,低着头,虽看不清他们的脸色,却偶尔能听到轻微的叹息声,这种声音像小皮锤,敲在身上很疼却不至死。
我不停的在祈祷:“佛祖保佑!”更为紧张的是徐方才,这毫无疑问。
等待着的人们谈论着病人的病情,从他们的语气和说话方式透露出,此刻每个人都是如此的善良,都是如此需要相互安稳,在压抑的缝隙中,传递着人应该有的那种感动和感恩,大家也都在鼓励着走向勇敢。
这一刻启迪了我很多。
不可否认,形式上看,我确实帮助了徐苗苗,但她更帮助了我,用她的危机簇拥着我进入另一个更深精神层面的思考,学会了换一个视觉去看待陌生人,更模模糊糊摸到了生死淡然的衣角。对,我岁数已经不小,却还在学会长大,感谢那个紧张的场景。
手术中的人很痛苦,等待手术中的人出来更痛苦。
同一时刻被推进手术室的病人,一个接着一个被推了出来,徐苗苗一点消息都没有。
空气慢慢凝固,徐方才变得有些焦躁,他已听不到家属们的声音,把注意力都集中在捕捉“徐苗苗家属”上,可惜,越是期待越等不来。
我起身走到住院部的院子里,试图用新鲜空气驱赶再次聚集而来的紧张感。我坐在院子外面的台阶上,天色已经变黑,楼上房间里的灯光从窗户里偷偷溜出来,把黑色调和成温黄色,迫使初春的冷空气散发出虚幻的暖意。
月亮升起,我看着它,心情竟然平复了很多。
就这样静静的坐着,不不知道过了多久。“苗苗怎么还没出来,会不会有什么问题,”身边传来徐方才的声音,声音中透露出煎熬。我这才想起来,我忽略了徐方才,他才是最紧张、最焦急、最担心的人,里面的徐苗苗与他虽无血缘,两者的连接却超越骨和肉。
“没事,没事,别太担心范主任亲自主刀,不会有问题的,”我站起来,示意一起进去等,一边走着一边对他说,医生不是说了嘛,这个手术本身时间就很长,别担心。
我还想找点其它的语言安慰他,但是,发现找不到更有说服力的词。其实,对于徐方才来说,他用自己的人生哲学在捕捉着信息,此时此刻任何语言对他都是无效的。多年以后,我,在医院外面等待着父亲从手术室里出来时,体会哪种感觉。
时间一分一秒在向前走,紧张和担忧成了杠杆,无限放大了每一秒的长度,甚至每一秒放大到一生的长度,佛经中所谓的一刹那竟然如此之长。
大概到晚上22:45分左右,我的手机突然响了。
是范主任发来的短信,上面只有几行简单段的字,却带来了我们一直期待的奇迹:“徐苗苗手术成功,马上转移到重症监护室。”
“佛祖保佑!”悬着的心放下了,我赶紧告诉徐方才。与此同时,等候区的广播也响起来:“四病区的徐苗苗手术结束,请家属继续在此等待。”
徐方才极速跑了过去,那一刻,我看到他眼角滚出了一行浑浊的泪,但是,他克制住了,泪水在眼角处转了几圈后,消失在眼眶内。
(八)
在四病区病房,我遇到了范医生,他刚换好衣服,正在办公室写手术记录。
“苗苗情况咋样?需要几天可以从重症病房出来,”我向他询问。
他告诉我,手术非常顺利,但是,需要在重症病房护理,这是大手术病人都需要的,一周后就可以转到普通病房,这段时间内家属不允许进去,只能每天早在规定时间里探视,种种病房里的医生会告知病人情况。
我从范医生办公室出来,找到了徐方才,把实际情况告诉了他。
安排好一切,我回宾馆休息,那一晚我睡得很香,梦中见到了家里许多人,大家都很快乐。
第二天一大早,医院,医生告诉我,徐苗苗已经醒过来了。
在重症监护室查完房出来,看到我站在门口,范医生说,“我带你进去看看孩子吧。”
我轻手轻脚的跟着他进去了,看到里面各种仪器,里面还有大概10多个孩子。徐苗苗睡着了,当我靠近她的时候,她醒了,揉了揉眼睛看到我叫了声阿姨。
“别说话,你安心呆在这里,我和你爸爸都会在外面等着你的,你要在这里住4、5天,这里有专人照顾你的,”我对她说。
她笑了,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她笑,很美!
徐苗苗的身体恢复的很快,4月9号早晨拆线,4月10日,我带着她回到宾馆,给她洗了个头,买了13号的票。
徐苗苗跟我说,“能不能带她去看看北京天安门?”
12号,我带着她和她父亲去了趟天安门广场和动物园,让她看了下北京的天安门。
这是一个温暖的春天。
对于我,一颗重担终于放下;对于徐方才,抢回了女儿;对于徐苗苗,死而后生;对于我们,一次人生洗礼。
(九)
按照医生的嘱咐,徐苗苗在家休养了一年后,徐方才带着她再次踏上去北京的火车,进行术后复查。
临走时候,我送他们去火车站。
徐方才问我:不知道苗苗以后能不能生孩子?
当时,我楞了一下,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
“去北京检查下,恢复的如何,主要孩子身体恢复好了才是最重要的,你问的这个,我实在不知道怎么说,我也不是医生,到了北京你问下医生吧。”
那是年春,又是一个温暖的季节。
赞赏
人赞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