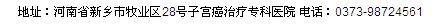赧水情第十三章1
姐姐自从因身体原因没有录上军校,三年来,一直闷闷不乐,沉默寡言,情绪低落,除了必要的工作接触,她几乎不和别人交往。眼见往日的同学们春风得意,而自己却命运不济,道路坎坷,她深感自卑,从不在街上逗留,从不与人沟通交流。只有我考上一中和逗弟弟玩耍时,她才露出了难得一见的笑容。她将自己的内心世界牢牢地封闭起来,连父母都不了解不知道她在想什么、思考什么。长期的精神压抑和心情郁闷,她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面无血色,形销骨立,无精打采。
母亲多医院医院检查治疗,限于当时的医疗条件和混乱的政治环境,姐姐的病非但不见好转,反而日见严重,已经转变成风湿性心脏病。父母看到大女儿病怏怏的样子,心疼不已,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昔日活泼可爱又是运动健将的爱女怎么会变成一个心脏病人。他们四处打听,寻医问药,也知晓风湿性心医院才有可能治愈,但治疗费用昂贵。
每天下班回家哪怕是深夜加班回来,他们都要去爱女的床边看看,或轻声询问或摸摸脉搏,他们没有经济实力又没有社会地位,只能以亲情以爱心呵护关爱自己的女儿。俩老曾多次商讨卖掉自家的住房陪伴她去长沙上海治疗的方案,可是,报纸上不断地传来长沙武斗的惨案和火车经常中断的消息,他们生性胆小,恐怕遭遇其他不测,而住房一时又没有找到合适的买家,所以,姐姐去外地治病的方案搁浅了。
学校停课闹革命的期间,我在家自学教材,做做习题,也看看小说书,干点日常家务活,生活比较有规律。姐姐感到很欣喜,她不止一次地给我说:“大弟啊,你不要看到现在一切都乱了套,中学大学都停止了招生,但是,这是暂时的。一个国家不可能不要知识,不要人才,中国不可能回到原始社会,将来国家一旦恢复了正常,是需要大批人才的,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你一定要牢记自己的使命,坚持不懈地朝着自己的理想和志向努力。”姐姐的每次谈话都言精意深,对形势的发展、对国家未来的分析判断有其独到的见解,一个不到十九岁的少女有如此深刻的洞察力,应该基于她良好的文化底蕴和善于观察、勤于思考的结果。
随着形势不断变化,局面越来越难以控制,人们狂热了,整个社会疯狂了。我觉得前途渺茫,将学习抛入九霄云外,每天和大妹愉快地干着家务活,制土砖捡砖头,建杂屋养小猪,挖药材挑锯木灰,忙得不亦乐乎。姐姐看在眼里,急在心里,脸色越来越难看,成天青着脸,时不时地讽刺几句:“老弟,你真聪明,现在当上了‘砖家’,当上了‘动物学家’了,恭喜你呀!”年少轻狂的我,不知轻重地顶撞一句:“我就是要这样,你能怎么样。”性格温和内向的她眼泪顿时“簌簌”地流下来。我一看心里着慌了,连忙向她道歉,她没有说一句话,只是连连叹气,我知道,姐姐认为我不理解她的殷切之心,彻底伤害了她。至今,我每想起这件事,心情异常的沉重,深深地后悔当初的幼稚和冲动。
经历了一年狂热的运动后,学校终于复课了,姐姐十分激动,比我还开心。她亲自陪着我去学校报名,送给我一本她珍藏多年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苏联小说,并特意将书中她做了记号的一段话声情并茂地念给我听:“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对人来说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回首往事的时候,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愧。”她念得热泪盈眶,我听得热血沸腾。她饱含着深情对我说:“老弟啊,父亲年近花甲又是个残疾人,母亲身体不太好,姐姐的病情堪忧,弟妹们又小,你是家里的顶梁柱,一定要努力学习,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你有能力了,才能好好地培养弟弟妹妹,让我们一家兴旺发达,让父母亲有个幸福的晚年。”我一边听着一边频频点头,当时我并不知道这是她的苦心,是她临终前的嘱托。
看着姐姐被病魔折磨成骨瘦如柴的模样,父母忧心如焚,又无法可想,没有任何医学知识的他们病急乱投医。医生说贫血,他们就买来贵重的鹿茸蒸母鸡给她吃;有人说打鸡血可治百病,他们就买一只雄壮威武的大公鸡,医院注射鸡血。种种违背医疗科学的荒唐行为竟然发生在号医院,当时的愚昧落后,可见一斑。
这种有百害无一利的治疗,导致姐姐的病情迅速恶化,一身浮肿,咳嗽不断,食不知味,难以下咽。临近过年时,她已经没有力气走动了,整天躺在床上。她没日没夜地咳嗽,先是痰中带有血丝,接着是半痰半血,睡不能卧,只能半躺着;后来她完全是大口吐血,只能整夜整夜地靠着床头地坐着。母亲的心绞痛又复发了,她和姐姐睡在同一张床上,母女俩的呻吟声咳嗽声此起彼落,似一曲心酸凄凉的音乐声声痛彻我们的心房。可怜的父亲强打起精神,拄着双拐带着我和大妹小妹准备过年的食物,三岁多的弟弟偎依在母亲和姐姐的身旁。一家人过了一个没有喜庆没有欢乐的春节。
年农历正月11日夜晚八点多钟,姐姐突然大口大口地吐血,“姆妈娘,姆妈娘”地喊个不停,一家人紧张得不得了,本来患心绞痛的母亲绞痛愈加剧烈,在床上翻江倒海似地滚来滚去。父亲连续劳累了十几天,已经身心交瘁,束手无策,他赶紧走到下街唐小乐家里购买蜂蜜,让姐姐喝蜂蜜热水止咳止血。唐妈妈和我母亲非常要好,她听说了姐姐的病情,立即赶来我家探望。她看到姐姐吐血不止,焦急不已,医院诊治。
恰巧,父亲早年的朋友杨师傅的儿子正在我家,小伙子年轻力气大,背医院,我和父亲、唐妈妈紧紧跟在后面。一路走小道田埂路,翻过一块山坡坟地,医院门诊楼。门诊楼大堂亮着一盏昏暗暗的吊灯,各个诊疗室房门紧闭,全无人影,异常的寂静阴森,令人毛骨悚然。我焦躁地走到挂号室前,用拳头敲打着挂号室窗口,好不容易窗口开了,一个中年女人绷紧着脸站在窗内,我边交钱挂号边问道:“有医生看病吗?”她递出挂号单,不耐烦地回答:“有人。”“嘭”的一声,她随手就把窗口关闭了。可能是我们的动作声响太大,或许是姐姐痛苦的呻吟声惊动了值班医生,一间诊疗室的门打开了。我们撑扶着姐姐走进诊疗室,在诊疗桌旁边的一把藤椅上坐下来。
这是一个瘦高个的中年医生,白大褂的左手臂上套着一个造反组织的红色袖章。他见我们进来,立即站起来打开诊疗桌的抽屉,从里面拿出一本红色的毛主席语录本放在胸前,表情严肃地对着墙上的毛主席画像虔诚地说:“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敬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敬祝完毕,他将红宝书放入抽屉里,坐下来开始诊疗。他静静地听完我们介绍了病情,摸了摸姐姐的脉博,又用听诊器在她的左右胸部游走了一番后,漫不经心地开了一张处方和住院证。我们急切地询问道:“医生,请问是什么病。”他含含糊糊地说:“可能是心脏病引起肺部感染。”我接过住院证和处方,快步走去交钱拿药,那位中年女人拿着处方对药房的女青年说:“今晚这个病人危险,开这么贵重的药,要么好得快,要么死得快。”我心里陡然一沉,腿都软了。我手里拿着八元钱的两粒药神色慌乱地走进诊疗室,医院没有开水,我只能给姐姐喂了一粒药干吞下去。然后,我们用藤椅抬着姐姐高一脚低一脚地走向住院楼二楼的病房。
整个院内漆黑一片,楼内也是静悄悄的,姐姐住的病房空无一人,没有看到一个医生,也没有见到一个护士,只有一声声“姆妈娘、姆妈娘、姆妈娘”的凄凉悲切地呼喊声划破了寂静冰冷的夜空。姐姐也许已经知道自己正面临着生离死别,死神随时会夺走她的生命,她舍不得生她养她的父母,舍不得朝夕相处至亲至爱的同胞手足,她只有竭尽全力呼喊表达心中的不舍,减缓心脏的痛苦。我们准备将姐姐移入病床上,她轻轻地摇头示意,表示自己根本不能平躺或半躺。我站在她坐着的藤椅的右侧,用左臂枕着她的头,右手紧紧握着她的手。父亲横坐在靠着墙壁的病床上,泪流满面,双手不停地拍打着床铺,无声地抽泣着。我抱着姐姐,不时地瞟一眼悲伤极致的父亲,我的心好痛好痛,口中止不住地呼唤着姐姐,只见她偏头看了我一眼,她的眼睛瞳孔放大,痛苦不堪地呼喊声越来越小。我隐隐感觉到姐姐命在旦夕,回天无力了。猛然,她的头向左一歪,重重地落在我的左手臂上。我泪如泉涌,大声呼喊:“姐姐,姐姐,姐姐……”她再无应答。我最亲爱的姐姐、我人生的导师在我的怀抱中撒手人寰了。这是我一生中最最悲痛的事,甚至超过后来父母亲的逝世。
良木文学